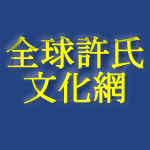全球許氏文化網 討論區索引 全球許氏文化網 討論區索引 許氏網路資訊及文章 許氏網路資訊及文章
 福建]許氏海軍世家 福建]許氏海軍世家 | 註冊才能張貼 |
| 樹狀顯示 | 新的在前 | 前一主題 | 下一主題 | 底部 |
| 張貼者 | 討論串 |
|---|---|
| charlie | 張貼於: 12月16日 11:55 |
管理員   註冊日: 06月28日 來自: 張貼數: 120 |
福建]許氏海軍世家 琴江村,座落於長樂市航城鎮,位於閩江入海口15公里的長樂洋嶼半島上,是烏龍江、馬江、琴江的匯流處,地勢險要,因此又被稱為三江口。 琴江村的村民都為滿族人,通行滿族的“旗下話”與福州本地區方言,並保留有滿人特有的生活習俗。
清代,福州開始只有八旗駐防部隊而沒有水師營。 該地由“三藩”之一的鎮南王耿精忠鎮守。 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和吳三桂一起舉起反旗,耿精忠聯合台灣的鄭氏在福建一帶向清軍發動進攻,清政府派康親王入閩平叛,琴江村的旗人先祖就在此時隨康親王入閩的。 “三藩之亂”以後,福建海防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視。 康熙十八年(1679)便派八旗的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二千零九十名官兵前往福州駐防,建立了八旗營,駐防在福州旗汛口和蒙古營一帶。 這個八旗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兵佔領台灣以前對防止海匪侵擾,鞏固東南沿海海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清兵進軍台灣的強大後盾。 ⑴雍正六年,將軍蔡良、副都統阿爾賽會同總督高其倬,議設三江口水師,奏報清廷,並要求從老四旗中抽調官兵攜眷屬進駐此地。 雍正六年(1729),清廷鑑於三江口的重要地理位置,歷來就為兵家必爭之地,加之出於監視和牽制駐防閩江口要鎮綠營的考慮,於是清征南將軍賴塔奉旨挑選513名旗兵進駐琴江,建了500多座的兵營,形成了正式的水師編制。 ⑵ 三江口水師旗營,可以算是當時福建最早的八旗水師,同時它也是直屬於清政府中央調配的四支水師之一,其最高長官即福州將軍。 它直接聽命於中央,不受地方節制,同時還有權監視地方,維護滿族對福建的統治,當時“四旗兩營駐紮在省城,控扼上下游各府,為閩省之中權” ,而福州將軍的職掌即“以四旗而兼統綠營”。 ⑶與此同時,三江口水師旗營的設置可以與臨近的閩安鎮相互協防,福州的閩安為扼守福建海洋之咽喉,外敵從這裡入侵,必從五虎門登陸。 因此它與洋嶼的三江口水師互為犄角之勢,“海舶之來必循五虎門以入,有閩安以捍禦於外,又得洋嶼以應援於內”。 ⑷也正是如此,清政府在雍正六年往洋嶼派駐了近六百的八旗官兵,以扼守福建咽喉和保衛台灣島。 ⑸ 福建近代海軍的搖籃 ——琴江與福建船政的血脈親情 明清時期東南沿海地區長期受到倭寇騷擾和海匪劫掠,沿海經濟受到很大影響,國無寧日,民不聊生。 而雍正帝也深感“國防至要”,“海軍第一”。 於是在雍正二年就著手在天。 鋤妒津籌建水師旗營,摸索建置經驗,隨後在杭州乍浦、福州、廠。 州建立水師旗營,強調“爾等。旗人宣識水務”,誠所謂“謀之深,求之嚴”。 ⑺旗營成立後強化訓練,在每年的十一月份要在大鯉魚山洗炮一次,並於春天的二月十五日肇三月一日,秋天的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一目演吹兩次海螺。 屆時四旗分派螺號兵在東西南北四門進行有計劃、有指導的練習。 該水師還於每年二、三、四、五月和十、十一月,按月分為八撥,輪流訓練。 屆時,協領一員,防禦、驍騎校四名,領催、砲手共二百名,攜弓箭、鳥槍、火藥等開赴洋嶼海域進行訓練,將軍、副都統輪流檢查巡視、在緝私船隊訓練完結後,用於海戰的水師要出動六艘大戰船、八艘小戰船在三江Et一帶不斷的進行操練。 此外,每遇到修造完畢,也還要進行試航訓練。 ⑻ 其次軍紀嚴明,全封閉不干預地方司法行政事務,專司訓練,與民秋毫無犯。 在冷兵器時代,就以槍砲、弓馬騎射、刀劍陣法俱全,具備了兩棲作戰的能力,因此在當時也可稱為精銳之師。 三江口水師旗營活動在海防的第一線,因此習水性為首要,加之瀕臨大江,這就為訓練游水提供了良好的場所,旗營子弟父帶子、祖帶孫、兄帶弟,在夏日午飯和晚飯後在江邊練習水性,相互幫教,相互照應。 隨著歷史的變遷,琴江人由於有著良好的基礎,成人後他們中的一批優秀的人從舊式的水師家庭,步入了福建船政學堂系統學習船政的理論與技能。 琴江村孕育了大量的中國近代海軍的優秀科技人才。 他們中有海軍艦隊司令、海軍少將、海軍艦長、大副、二副、輪機長等各級海軍專業人員,及電訊、船舶、鐵路、開礦、魚雷、測量、無線電、電報、航空等各方面的專家。 福建船政學堂為琴江村孕育出許多的海軍世家。 而這些海軍世家秉承了船政文化及嚴謹家風,為福建船政文化爭光添彩。 福建省長樂市琴江的許氏一門延續了八代的海軍,出現了多位的將軍,並有多人曾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該家族中最有名的要屬曾任國民政府艦隊司令的許建廷,此入當時在福建的海軍界相當有影響力的。下面具體介紹一下許氏海軍世家的變遷: 許贊賢(1856—1912),光緒丁亥附生,馬尾船政學堂政稿吏,五品軍功。敘官縣丞加同知銜。民國十四年,政府追贈“建威將軍”。許贊賢為許氏家族中最早踏入近代海軍的先祖。 許贊虞(1862—1930),光緒乙酉附生,馬尾船政後學堂畢業,五品項戴,選用主簿,負責監造平遠艦,船政前後學堂教員、福問格致書院教員、直隸保定大學堂教員、湖北礦化學堂學監、興國州大冶縣煤鐵等礦師,民國十四年,任海軍部上校科員。 許贊週(1864—1916),光緒甲子附生,馬尾船政前學堂畢業,後奉命派往測繪福建上游地圖,獲五品頂戴敘官縣丞,歷任京漢鐵路工務段長、漳廈鐵路工程師。 許建藩(1881—1942),光緒乙亥附生,馬尾船政前學堂畢業,充京漢鐵路站長,民國三年海軍部科員、副官,十五年授海軍造船少監。 許建廷(1887—1960),光緒丁亥附生,馬尾船政後學堂,十六屆畢業生,專業為駕駛、天文、戰術、水雷、魚雷等,隨後留學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格林威治、鮑特司密夫)?學成歸國後在清海琛艦任教練官,湖鷹、聯鯨艦管帶。辛亥革命後率艦北伐,後任建安、靖安、海籌等艦艦長,民國二年授官中校,五年晉上校。在其任靖安艦艦長時,經常制止象山人的械斗等,並打擊沿海的海盜,使沿海的商船為之安逸,故當時家家立長生祿位祝之。 1922年曹錕賄選大總統時,許建廷任海籌艦艦長聯名通電發動討賄選運動。第…次直奉戰爭,吳佩孚以“武力統一中國”、許時任海籌艦艦長,領銜聯合“永績”、“健康”兩艦及“列字”艦艦長通電全國,反對“武力統一”並率艦南下,脫離直系,孫中山通電錶示肯定,並言:“文當竭其棉薄,相與戳力同心,共紓國難”。 民國十二年晉升為少將,民國十三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率海籌艦官兵從日本手中接收青島,中外交口稱譽,授二等文虎、嘉禾勳章。民國十四年擢升為中將,第二艦隊司令,旋任閩海關監督兼交涉員。解放後1956年被長樂縣政府聘為縣政協委員,1960年病逝。 此外,許氏一門還有像許贊祿、許贊普、許建鑣、許建鐘、許建忠、許建鼎等許氏後人,他們畢業於菸台海軍學校、福州陸軍學校,隨後都為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中的多人曾任海軍的艦長,其中許建鑣更為國民政府的少將副官(台灣)。 |
| andy | 張貼於: 08月13日 13:56 |
管理員   註冊日: 06月28日 來自: 張貼數: 173 |
自我、他者與國家:福建琴江滿族的認同 http://www.jxcu.com/guanlitizhi/200807/29-293105.shtml
琴江滿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師旗營官兵的後裔。 據其家譜和墓碑的記載,他們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漢軍旗人。 1979年,琴江人集體要求將民族成份由漢族改為滿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滿族村。 本文在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考察並分析了漢軍旗人的認同意識以及隱藏在認同意識背後的歷史傳說和文化淵源,並通過分析認同過程中自我、他者、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指出了現代國家背景下少數民族認同的動態特徵。 關鍵詞:滿族漢軍旗人歷史記憶認同作者劉正愛,女,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地址:北京市,郵編100871。 一、問題的提出本文以福建省長樂市琴江滿族村的八旗漢軍後裔為例,通過他們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強烈要求修改民族成份並於1979年建立滿族村的過程,考察國家框架之下少數民族認同的動態特徵。 目前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滿族人口已居第二位,僅次於壯族。 縱觀幾十年來滿族人口的變化,我們看到,從1953年到1964年滿族人口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分別為240萬和270萬人,1982年滿族人口超過了430萬人,而到了2000年已經高達1068萬人。 有研究表明,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遼寧省錦州地區大約22.6萬名滿族人當中,有10%是八旗滿洲的後裔,其餘的90%為八旗漢軍的後裔。 參見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p.279.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關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滿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可歸於多種原因,但主要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滿族地位降低,很多滿族人隱瞞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直至80年代落實民族政策後才又重新申報為滿族。 滿族作為一個正式的民族名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此之前主要是用旗人、滿人、滿洲人等稱呼。 眾所周知,八旗制度是清代的軍事、社會制度。 八旗分為八旗滿洲、八旗漢軍、八旗蒙古,旗人是指包括家屬在內的所有八旗成員。 非八旗成員則被稱為民人(漢人)。 也就是說,旗人和民人是圍繞著八旗制度產生的兩個相對應的概念。 因此,漢軍旗人雖然與民人具有相同的文化譜系,但由於他們被編入了八旗,因此他們與民人屬於不同的範疇,即他們是被定位在旗人這個範疇裡的。 關於漢軍旗人的民族歸屬問題,過去曾經展開過一些討論。 參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國內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64年印行,第134-136頁。 上世紀8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王鍾翰先生提出:“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王鍾翰:《滿族史研究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 這一觀點後得到史學界的廣泛認可。 但在實際生活當中,很難做出這樣明確的區分。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後民族政策的變化帶來的結果是,只要是子孫三代(甚至是姻親)中有一人是旗人,就可以報滿族。 但也有一些漢軍旗人,雖然沒有出旗,卻仍堅持認為自己是漢族,不承認自己是滿族;反過來,有的雖已出旗為民,但仍認為自己是滿族的漢軍旗人,而且這樣的人還很多。 重要的是,無論本人的民族意識如何,如果得不到行政上的認可,就不能享受少數民族的待遇。 換句話說,在中國,個人的民族認同與伴隨著制度性保障的民族成份並不總是完全一致的。 這是因為,國家主導的民族識別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行政性、制度性的“民族”。 巴特的族群邊界論所代表的族群(ethnicity)研究認為,族群性是自我和他者互動關係的產物,它受雙方的製約;在邊界的形成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文化特徵還會不斷發生變化。 參見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10. Universitesforlaget, 1969。 在中國,雖然也存在上述情況,但是國家的行政性、政治性因素顯然比文化因素重要得多。 科恩也曾指出:不應該把族群性看做固有不變的東西,而應當把它當做根據周圍的情況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像或可操作的歸屬意識來看待,族群性具有隨機性、戰術性和工具性特徵,它是任意的和可變的。 參見Avner Cohen, “Introduction: 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A. Cohen (ed),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k Publications, 1974。 科恩強調的這種隨機性和工具性特徵,在中國是要經過國家的行政性及製度性的認可才有可能實現的。 美國學者赫瑞通過對中國彝族的研究,認為族群性的真實本質是三種界定相混合的產物。 族群的界定者包括族群成員自身、鄰近族群成員和國家。 在中國,國家掌握著民族識別以及資源配置的最終決定權。 參見\[美\]斯蒂文•赫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頁。 日本學者毛里和子認為,中國的“民族”是自上而下“建構”出來的。 參見\[日\]毛里和子:《從周邊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這個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要看到,它並不是單方面的建構。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少數民族對國家所建構的“民族”的積極響應。 另一位日本學者鈴木正崇在強調少數民族被國家創造這一點時,不僅注意到國家與少數民族之間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互動,而且也注意到外在與內在兩個不同的力學角度。 參見\[日\]鈴木正崇:《被創造的民族——中國的少數民族與國家形成》,\[日\]飯島茂編:《“民族”與國家的抗爭——人類學的視野》 ,日本學術出版會1996年版,第212頁。 筆者認為,只有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視角放進我們的視野,而不是只注重某一個單方面的視角,才能真正了解當代中國少數民族的本質。 滿族的認同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備受歷史學家的重視。 柯喬燕(Pamela Crossley)、愛德華•路斯(Edward JM Rhos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通過文獻分析,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清代或清末民初滿洲人的認同特徵。 參見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0;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這些成果為研究當代滿族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視角。 本文為全文原貌未安裝PDF瀏覽器下載安裝原版全文琴江滿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師旗營官兵的後裔。 據其家譜和墓碑的記載,他們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漢軍旗人。 1979年,琴江人集體要求將民族成份由漢族改為滿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滿族村。 本文在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考察並分析了漢軍旗人的認同意識以及隱藏在認同意識背後的歷史傳說和文化淵源,並通過分析認同過程中自我、他者、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指出了現代國家背景下少數民族認同的動態特徵。 關鍵詞:滿族漢軍旗人歷史記憶認同作者劉正愛,女,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 地址:北京市,郵編100871。 一、問題的提出本文以福建省長樂市琴江滿族村的八旗漢軍後裔為例,通過他們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強烈要求修改民族成份並於1979年建立滿族村的過程,考察國家框架之下少數民族認同的動態特徵。 目前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滿族人口已居第二位,僅次於壯族。 縱觀幾十年來滿族人口的變化,我們看到,從1953年到1964年滿族人口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分別為240萬和270萬人,1982年滿族人口超過了430萬人,而到了2000年已經高達1068萬人。 有研究表明,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遼寧省錦州地區大約22.6萬名滿族人當中,有10%是八旗滿洲的後裔,其餘的90%為八旗漢軍的後裔。 參見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p.279.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關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滿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可歸於多種原因,但主要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滿族地位降低,很多滿族人隱瞞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直至80年代落實民族政策後才又重新申報為滿族。 滿族作為一個正式的民族名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此之前主要是用旗人、滿人、滿洲人等稱呼。 眾所周知,八旗制度是清代的軍事、社會制度。 八旗分為八旗滿洲、八旗漢軍、八旗蒙古,旗人是指包括家屬在內的所有八旗成員。 非八旗成員則被稱為民人(漢人)。 也就是說,旗人和民人是圍繞著八旗制度產生的兩個相對應的概念。 因此,漢軍旗人雖然與民人具有相同的文化譜系,但由於他們被編入了八旗,因此他們與民人屬於不同的範疇,即他們是被定位在旗人這個範疇裡的。 關於漢軍旗人的民族歸屬問題,過去曾經展開過一些討論。 參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國內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1964年印行,第134-136頁。 上世紀8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王鍾翰先生提出:“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王鍾翰:《滿族史研究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頁。 這一觀點後得到史學界的廣泛認可。 但在實際生活當中,很難做出這樣明確的區分。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後民族政策的變化帶來的結果是,只要是子孫三代(甚至是姻親)中有一人是旗人,就可以報滿族。 但也有一些漢軍旗人,雖然沒有出旗,卻仍堅持認為自己是漢族,不承認自己是滿族;反過來,有的雖已出旗為民,但仍認為自己是滿族的漢軍旗人,而且這樣的人還很多。 重要的是,無論本人的民族意識如何,如果得不到行政上的認可,就不能享受少數民族的待遇。 換句話說,在中國,個人的民族認同與伴隨著制度性保障的民族成份並不總是完全一致的。 這是因為,國家主導的民族識別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行政性、制度性的“民族”。 巴特的族群邊界論所代表的族群(ethnicity)研究認為,族群性是自我和他者互動關係的產物,它受雙方的製約;在邊界的形成過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文化特徵還會不斷發生變化。 參見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10. Universitesforlaget, 1969。 在中國,雖然也存在上述情況,但是國家的行政性、政治性因素顯然比文化因素重要得多。 科恩也曾指出:不應該把族群性看做固有不變的東西,而應當把它當做根據周圍的情況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像或可操作的歸屬意識來看待,族群性具有隨機性、戰術性和工具性特徵,它是任意的和可變的。 參見Avner Cohen, “Introduction: The Lesson of Ethnicity”.In A. Cohen (ed), Urban Ethnicity. London: Tavistok Publications, 1974。 科恩強調的這種隨機性和工具性特徵,在中國是要經過國家的行政性及製度性的認可才有可能實現的。 美國學者赫瑞通過對中國彝族的研究,認為族群性的真實本質是三種界定相混合的產物。 族群的界定者包括族群成員自身、鄰近族群成員和國家。 在中國,國家掌握著民族識別以及資源配置的最終決定權。 參見\[美\]斯蒂文•赫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頁。 日本學者毛里和子認為,中國的“民族”是自上而下“建構”出來的。 參見\[日\]毛里和子:《從周邊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這個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要看到,它並不是單方面的建構。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少數民族對國家所建構的“民族”的積極響應。 另一位日本學者鈴木正崇在強調少數民族被國家創造這一點時,不僅注意到國家與少數民族之間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互動,而且也注意到外在與內在兩個不同的力學角度。 參見\[日\]鈴木正崇:《被創造的民族——中國的少數民族與國家形成》,\[日\]飯島茂編:《“民族”與國家的抗爭——人類學的視野》 ,日本學術出版會1996年版,第212頁。 筆者認為,只有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視角放進我們的視野,而不是只注重某一個單方面的視角,才能真正了解當代中國少數民族的本質。 滿族的認同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備受歷史學家的重視。 柯喬燕(Pamela Crossley)、愛德華•路斯(Edward JM Rhos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通過文獻分析,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清代或清末民初滿洲人的認同特徵。 參見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0;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這些成果為研究當代滿族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視角。 本文為全文原貌未安裝PDF瀏覽器下載安裝原版全文作為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定宜莊、胡鴻保的合作研究則把視線投向了當代滿族的認同問題。 他們通過文獻史料的考證和田野調查,將歷史研究應用到了具體個案的分析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參見定宜莊、胡鴻保:《“有入有出”與“融而未合”——對共同體形成問題的若干思考》,《滿學朝鮮學論集》,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版;《鷹手三旗的後裔:對北京市喇叭溝門滿族鄉的調查與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淺論福建滿族的民族意識》,《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虛構與真實之間——就家譜和族群認同問題與〈福建族譜〉作者商榷》,《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定宜莊:《對福建省滿族歷史與現狀的考察》,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調查報告》第8號,1998年。 本文將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進一步闡釋國家與少數民族的互動關係以及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認同的特徵。 二、琴江村歷史:城牆之內與城牆之外琴江村位於福建省東部閩江南岸的烏龍江、馬江、白龍江匯合處,是省內唯一的滿族村,行政上屬於長樂市,距閩江口15公里。 流經這一段的閩江宛如一把古琴,故名琴江。 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為了發展和完善八旗駐防制度,從駐防於福州的老四旗中抽調了513名八旗漢軍官兵攜眷進駐琴江,圍地築城,建立了“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也稱“營盤裡”)。 這一段歷史,在筆者收集到的家譜中也有所反映。 根據《琴江許氏家譜》(1928年編)記載,許氏始祖聖公於天聰崇德年間編入漢軍鑲白旗,二始祖義起公於康熙十五年(1677)平定三藩之亂後入福州,三世祖宗華公於雍正七年十月移居琴江。 楊家家譜《四知堂楊家支譜——次房》中,雖沒有“漢軍旗”的字樣,但也提到其祖先原籍遼東,後隨靖南王輾轉山東、廣東等地,“入閩而居”。 此外,根據賴氏家譜記載,賴氏先祖賴通照在明中葉寄籍遼陽,清初以功隸旗下,“從龍入關”,故世為漢軍正黃旗人。 對於沒有家譜的人家來說,墓碑是唯一可以證明其祖籍的資料。 許多刻有“遼東”、“鐵嶺”、“延陵”、“三韓”字樣的墓碑至今還散見於荒山野嶺之中。 村民們以這些墓碑為依據來追本溯源,認定自己的老家在東北。 “三韓”墓碑以樸、李、金、崔四姓居多,村里人認定他們是清初入旗的朝鮮人後裔,但現無法找到支持這種說法的依據。 而有些歷史學家則認為“三韓”是一個地名,指的就是遼寧。 根據2003年2月13日定宜莊的口述。 目前琴江村有157戶,總人口為395人。 其中,滿族222人,漢族171人,苗族2人(據2002年的調查數據)。 這些年,出外打工人員逐年遞增,目前住在村里的只有200多人。 耕地面積還不足60畝,主要生活來源靠國內外的匯款和賣蔬菜所得的微薄收入。 三江口水師旗營與其他駐防地一樣,也是從建造特殊的空間開始的。 旗營圈地近5000平方米,建有5米高的城牆,城牆內有12條街,500套兵丁住房(共1321間)。 ②參見定宜莊:《對福建省滿族歷史與現狀的考察》,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調查報告》第8號,1998年。 1958年大躍進時期,城牆被拆毀,但城內建築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結構,尤其是首里街和馬家巷,至今還保留著舊時的風貌。 雖然水師旗營的城牆沒有把城內和城外的社會空間絕對隔離開來,但是作為旗人的生活空間,城裡在文化、政治與社會方面還是具有與城外不同的一些特徵。 在語言方面,18世紀中葉由朝廷推廣的“國語旗射”,給水師旗營的漢軍旗人也帶來一定的影響。 從水師旗營初建時起,清廷就派員外郎到此地,專門教授滿文滿語。 如果在福州將軍面前不能用滿語介紹自己,就會被免去職務,滿語說得好的則有可能晉升為官。 據定宜莊考察,直到道光朝(1821-1850)福州將軍至此地閱操時,該水師中還有能用滿語與將軍對答的佐領。 |
| 樹狀顯示 | 新的在前 | 前一主題 | 下一主題 | 頂部 |
| 註冊才能張貼 | |